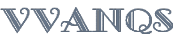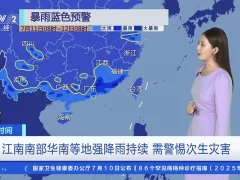常常有这样的时候,偶然地读到一句话,心都会猝然地一紧,一动,甚至是一痛,好像是已在潜意识中驻留了很久,却一直没有说出来的那一句;也好像是冥冥中已遗忘了很久,又忽然浮现出来的那一声。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靡靡。”
《诗经》上的这一句,是在中学时候读到的。那是一个风雨绵绵的黄昏,雨下得如泣如诉,如烟如雾,无边无际,无休无止。那天我经过小时候住过的旧居,房已拆,河已填,荒芜的瓦墟边上,一颗很孤寂的柳树在雨中绿得无法表达。那天偶然地翻到,读到了这一行诗。
几千年前的某一个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却会留下如此相似的一种感觉与心境。就像遇见那一刻的另一个自己,一个超越了时空的灵魂。
“我不认识你,可是我要谢谢你。”
那是一个安宁的午后,看一张报纸,读到“无偿献血”广告词的这一句。放下报纸,有好几分钟恍然若失。窗外阳光灿烂,有歌声正散入云天。
最好的话,最真的情,都是质朴的。简单的,直接的,坦率的,真心实意的,无须说明的。
读到这样的话,写出这样的话,都是一种幸福。
一种安安静静的幸福,就像窗外的蓝天,蓝得一无所有的幸福。
“请再骗我吧,请你继续骗我吧。”
一部电影,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电影的最后,被幸福地欺骗着的女人,在知道被欺骗之后,对男人这样无限幸福地低语。
也许是祈求,也许是无奈,也许是游戏的陶醉,也许是清醒的选择。
也许,人生有些错,你不犯这些错,就是最大的错。
“我们在河岸上静静地走着,你告诉我你已经死了,就在昨天。”
怪异的小说,怪异的氛围,怪异的平平静静中透出的强烈的危机,玄机与杀机。
但再读过,感到的,却是无悲无喜的平淡心情。
生死相隔,的确就应该如此简单。
死,是每个人历程中最相同、最平常、最可信、最不值得的一种事实。
对最正常的事实,只需漫不经心。
读过一首诗,写的是雪,关于在纷纷扬扬的雪中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浮现又消失的间断的回忆;关于在雪的闪亮的寒意中,想起《大屠杀》和乔伊斯的《死者》的恍惚思绪。最后一段是:
那一年我三岁。母亲抱着我,院子里有一棵树。
后来我们不住在那里——
母亲在1982年死去。
像轻轻的一声叹息。
最强烈的感动,如同风暴的中心,不是呼啸倾诉,而是奇异的静默。
寂静中爆发出来的凄厉的声响和凄厉的声音小时之后的无边寂静,都会震撼人们的心。
每一个时代,民众的心态都各有特点。他们自然是复杂芜杂的,但也有某种简单清晰的体现形式。比如,一句时代最流行的歌词,最流行的诗句,就是这一种心态的模糊却深切的烙印。
比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比如北岛的“我不相信”;
比如崔健的“一无所有”;
比如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
我相信,每个伟人,每个需要自己被后人记住的人,都需要一句话,那样的一句话,作为自己的某一种象征。
无论凯撒的:我来到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
无论斯巴达英雄的:我会死的,假如我还活着。
无论瞿秋白先生走进刑场时说的:此地甚好。
无论在空难中消失的徐志摩先生写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无论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
无论弘一法师的临终偈语:悲欣交集。
很多年以前的一个夏夜,我住在一个陌生的小城市的小旅店中,无聊之余,在楼下买了只口琴,在阳台上,独自轻轻地吹。周围,是一片很大的新社区,夜已深,几乎所有的楼房都已幽暗寂静,一曲奏完,也说不清楚是那一幢楼的哪一个窗口,轻轻地飘来一阵笛子的乐声,就像一种神奇的回声。那一夜,淡淡轻轻的旋律,回荡了很久。
我始终不知道那一个吹笛手是谁,但他(她)不再陌生。
那一个,就像那一句。
是我们等待了很久的东西。
也许就是我们自己。